2019年伊始的欧洲,传统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家领导人,各自遭逢国内和党内反对势力的挑战。默克尔在党内交棒、马克龙的 民调低落、特蕾莎·梅则是刚躲过不信任投票的逼宫,脱欧的B计划生死未卜。落难的欧洲三巨头,相对于意大利副总理、极右派联盟党领袖 和波兰内政部长元月初在华沙的记者会上宣称,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新欧洲”,已经为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和未来欧盟的走向,释放 出“向右走”强烈的政治讯号。
首先,今年3月底英国脱欧的情势动荡不安将近三年,仍然没有落幕;欧盟其他国家“知道英国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英国到底要什么”,而 最大的受害者,则莫过于和北爱尔兰接壤的爱尔兰,以及有英法海底隧道连接伦敦和巴黎的法国。此外,5月又适逢欧洲议会每五年一次的选 举,5亿选民第一次在没有英国的情形下选出议员,而选举的席次也将从现在的751席减少到705席。目前由亲欧盟、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组成 的执政联盟(476席)和反对党(275席)的态势,已经随着最近几年在法国和德国、荷兰、波兰、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其他前东欧国家(例 如捷克和匈牙利)右派政党的崛起、甚至取得执政权,一个正在“向右走”的欧洲,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将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政治学的理论来说,“左派”和“右派”所谓的「意识型态」(ideology)可以是一套逻辑连贯、具有系统的理念体系,也可以是一种 提出“阶级意识”、或信仰系统的政治世界观。从左到右的政治意识型态的光谱,已经是取得政治影响力的思维模式,并且过去百年来,在欧 洲各国也有具体的实践。不同的意识型态,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价值的选择;“自由”未必代表道德高尚,“保守”可能是传统观念价值的维 护。
其次,政治的意识型态影响欧洲“向右走”的政治走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其与各成员国家执政党的政策思维的连结。左派政党对于 加税、非核、大政府(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优先的坚持,相对于右派政党的减税、拥核、小政府、经济发展优先的主张,给予选民更多不同 的政治抉择。
虽然政府的政策伴随着执政权力的此起彼落,行之有年,然而,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国所引起贫富愈来愈悬殊的阶级抗争,以 及世代对立,成为各国政府的烫手山芋之际,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东西方“种族”和“宗教”因素,才是当前探讨欧盟“向右走”必须检视 的深层原因。
就此而言,影响欧洲国家“向右走”最重大的两个事件,莫过于2001年的远因和2010年的导火线。前者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自杀式恐 怖攻击,后者则是2010年12月发生于北非,延烧到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
虽然都不是发生在欧洲,美国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反恐战争,近年来欧洲各国大大小小的恐攻,直接间接形成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 明的正面冲撞。而从民生经济凋敝到反对极权统治,乃至于欧美国家介入,影响所及,利比亚独裁统治者格达费之死,利比亚陷入内战,执政 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当年受审到前年获释,国内政治动荡不安,特别是迄今尚未结束的叙利亚内战,更造成数百万计的难民离乡背井, 逃到欧洲各国。
一方面,数百万难民的安置收容,超过欧洲国家的负荷,引起欧盟成员国家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代表四分之三信徒的逊尼派沙地阿拉 伯,与代表少数什叶派的伊朗,中东双强竞逐的过程,除了伊斯兰教派的争斗,这是欧美国家和俄罗斯见缝插针,各显神通的场域。
两个重大事件都造成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难民透过各种路径前进欧洲,对于以重视人权着称于世的欧洲国家,难民的安置收容只是起点 。穆斯林在欧洲各国的落地生根,才是让欧盟国家必须接受政经、社会之外,“不能说出口”的种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随着经济情势和治安的 恶化、特别是一次又一次的恐攻,变成欧洲右派政党滋生成长的政治温床。
展望2019年的欧洲大势,德国、法国,以及英国所扮演“领头羊”的角色退位,中道“拼经济”的动能必然因而受到不利的影响;而欧洲 议会做为欧盟唯一由民选政治人物组成的机构,5月的选举将会是观察欧洲政治形势的重要指标。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反移民”、“反伊斯 兰”、或甚至是“反犹太”的政策口号,将会持续萦绕在欧洲的天空,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

 Iteca Exhibitions
Iteca Exhibitions 长城润滑油
长城润滑油 German Machine Tool Builders Association
German Machine Tool Builders Association 延长石油
延长石油 3M制造业
3M制造业 陕煤化工集团
陕煤化工集团 HUAWEI
HUAWEI Dahua Technology
Dahua Technology 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 Gemtique
Gemtique KUNVII
KUNVII PALEXPO
PALEXPO IAA Show
IAA Show LASTON
LASTON 中杭贸易
中杭贸易 PV EXPO
PV EXPO Etek Europe
Etek Europe 陕西有色金属
陕西有色金属 QIIE青岛进博会
QIIE青岛进博会 维远光伏产业
维远光伏产业 Time Out Group
Time Out Group IFEMA
IFEMA 天元化工
天元化工 National Media
National Media 吉祥星科技
吉祥星科技 Dowpol Chemical
Dowpol Chemical 海康威视-HIK VISION
海康威视-HIK VISION Hannover Messe
Hannover Messe TOSHIBA
TOSHIBA Productronica
Productronica HealthCare
HealthCare 深圳会展中心
深圳会展中心 大唐旗舰店
大唐旗舰店 Soul Game
Soul Game 神木职教中心
神木职教中心 Sinopec
Sinopec 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央视对话:为什么是深圳?
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央视对话:为什么是深圳?![2021博鳌中国传统文化高峰论坛拍卖会[崔葡萄]再创辉煌](http://www.18sz.com/file/upload/202110/20/1401393534441.jpg) 2021博鳌中国传统文化高峰论坛拍卖会[崔葡萄]再创辉煌
2021博鳌中国传统文化高峰论坛拍卖会[崔葡萄]再创辉煌 中航工业直升机:新生活 新高度
中航工业直升机:新生活 新高度 冬季入浴前需提前预热浴室
冬季入浴前需提前预热浴室 记者带你去看澳门光影节 五彩斑斓
记者带你去看澳门光影节 五彩斑斓 上海进博会:创意微视频《汇•惠》
上海进博会:创意微视频《汇•惠》 Undersea Defence Technology
Undersea Defence Technology 崔培鲁画牡丹花
崔培鲁画牡丹花 印度嵌入式展产品展示
印度嵌入式展产品展示 2021年意大利米兰国际艺术展览会
2021年意大利米兰国际艺术展览会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玲珑塔店正式开业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玲珑塔店正式开业 万上遴优秀作品展
万上遴优秀作品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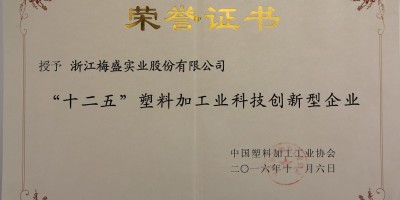 梅盛实业企业荣誉
梅盛实业企业荣誉 China Forged Valves Factory Tour
China Forged Valves Factory Tour 人文珠宝 - 文化传承
人文珠宝 - 文化传承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海南免税购物火爆
今年十一国庆假期海南免税购物火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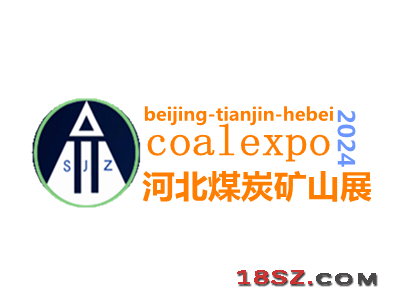 2024河北采煤技术展览会|河北煤炭设备展会|河北煤业展
2024河北采煤技术展览会|河北煤炭设备展会|河北煤业展 展会怎么选择?UFI认证展会了解下
展会怎么选择?UFI认证展会了解下 专供地铁等基建H型钢
专供地铁等基建H型钢 2024深圳医博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2024深圳医博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上海国际医用防护用品展览会将于6月30日召开
上海国际医用防护用品展览会将于6月30日召开 合肥专业生产烧结砖厂家 园林行道砖 广场砖 厂家直销
合肥专业生产烧结砖厂家 园林行道砖 广场砖 厂家直销 彩墨簕杜鹃-深圳(竖)
彩墨簕杜鹃-深圳(竖) 个人艺术钻石展预约
个人艺术钻石展预约 意大利里米尼城市介绍
意大利里米尼城市介绍 纽伦堡 - 玩具都城
纽伦堡 - 玩具都城 慕尼黑 - 伊萨尔河畔的酒都
慕尼黑 - 伊萨尔河畔的酒都 法兰克福 - 欧洲金融中心
法兰克福 - 欧洲金融中心 迪拜 - Dubal
迪拜 - Dubal 俄罗斯 - 战斗民族和套娃的国家
俄罗斯 - 战斗民族和套娃的国家 葡萄牙 - 软木塞之乡
葡萄牙 - 软木塞之乡 西班牙 - 斗牛士的故乡
西班牙 - 斗牛士的故乡





